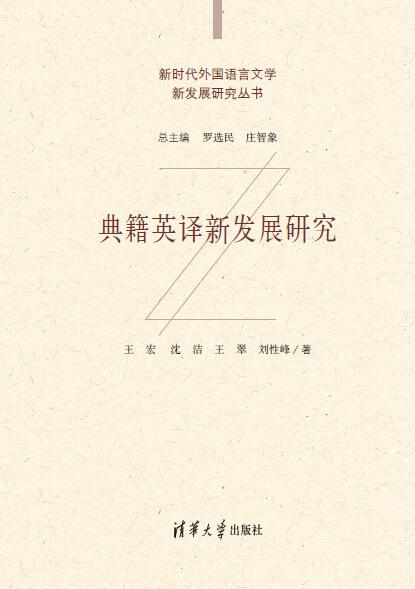





定价:148元
印次:1-2
ISBN:9787302573142
出版日期:2021.08.01
印刷日期:2022.10.31
图书责编:白周兵
图书分类:学术专著
本书对中国典籍英译学科背景及发展历史,尤其是典籍英译在新时代(2000—2019年)取得的新进展进行了全方位梳理和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新时代典籍英译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实践。本书信息量大,研究方法独特,全面、客观地总结了新时代典籍英译在各领域所取得的新成绩,深刻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高度探讨了典籍英译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关心和从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专家学者、高校师生等。
王宏,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中外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荣获省部级科研优秀成果奖多项。已出版发表学术成果130项,其中在《外国语》、《中国翻译》等外语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6篇,在国内外各知名出版社出版著译作44部。
本书书名为《典籍英译新发展研究》。开宗明义,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何为“典籍”。根据《辞海》(夏征农,2000:831)给出的解释和定义:“典籍”乃“国家重要文献”;“典籍”为“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由此推知,“典籍”一词有两层义项:“一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目前,学界大多认可将1911 年之前出现的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重要文献和书籍视为“典籍”。据此,我们在从事典籍翻译时,不但要重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还要关注中国古典法律、医药、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作品;不仅要翻译汉语典籍,也要翻译其他少数民族典籍。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完整地翻译中国典籍。 回顾中西交流史,中国和欧洲的文化接触可以上溯到公元前数百年,但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则开展较晚。13 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曾经到过中国,并撰有游记传世。1590 年,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翻译的《明心宝鉴》(Precious Mirror of the Clear Heart)是中国文学译成欧洲文字的第一本书。16 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华。他们出于传教目的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广泛涉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和科技典籍,通过翻译、评论、书信等形式向西方读者描绘出一幅具有高度文明和特殊智慧的异域生活画卷,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中国热”。据黎难秋(2006: 584)考证,“利玛窦实为西人译中国经籍之祖。1593 年,他最早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并寄回国内”。这一译本虽已失传,但从同时代西人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赞誉中可以...
上 篇
第一部分 典籍英译理论发展期(2000—2009 年) ???????3
第1 章 概述(一) ???????????????????????????????????????? 5
1.1 学术资源数据分析 ????????????????????????????????????? 5
1.1.1 发文数量 ??????????????????????????????????????????????????????? 6
1.1.2 热点议题 ??????????????????????????????????????????????????????? 6
1.1.3 博士学位论文 ???????????????????????????????????????????????? 7
1.2 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趋势 ????????????????????????????? 10
第2 章 文学典籍英译(一) ????????????????????????????11
2.1 引言 ?????????????????????????????????????????????????????? 11
2.2 古典诗词英译 ?????????????????????????????????????????? 11
2.2.1 主要概念与理论观点??????????????????????????????????? 11
2.2.2 重要成果 ?????????????????????????????????????????????????????... 查看详情



 电子书
电子书
 在线购买
在线购买
 分享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