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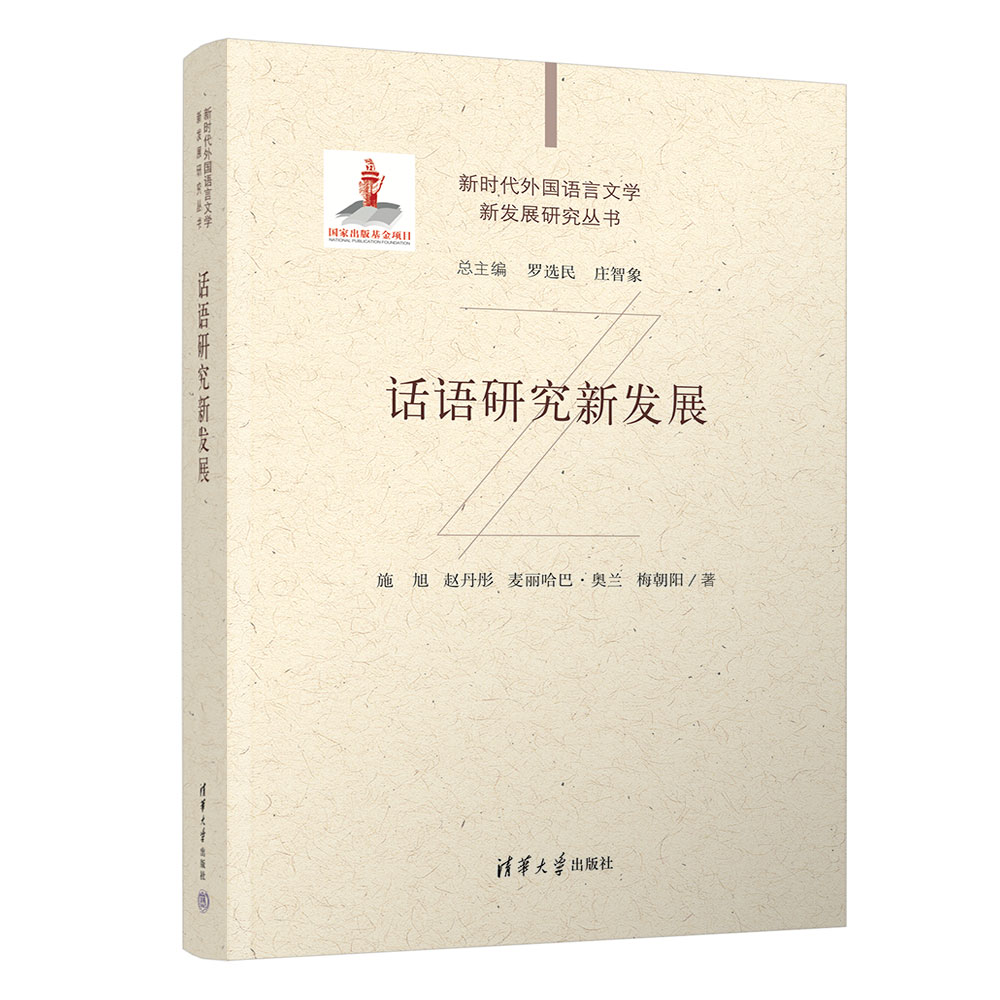



定价:108元
印次:1-1
ISBN:9787302624332
出版日期:2022.12.01
印刷日期:2023.01.13
图书责编:倪雅莉
图书分类:学术专著
《话语研究新发展》旨在研究近十年来,我国话语研究的发展现状、未来发展的趋势与路径,将在梳理话语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同时,重点探讨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并从安全话语、经贸话语、媒体话语等领域给出实证研究与评价,助力中国突破西方学术舆论围堵。本书将帮助对话语研究领域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和相关学生理解,并学习以多元文化为视角的话语理论体系,了解话语的文化特质和中国话语的现实与规律,助力构建、创新中国话语研究体系,深化和拓展话语研究的途径。
赵丹彤,女,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管理学学士(双学位),曾于2015年至2016年赴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访学。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化话语研究、商务话语研究、危机传播研究等。
前言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包括传播学、新闻学、话语分析、文学批评、修辞学、语言学的学者和学生,报告过去20年里国内话语研究的一些新趋势、新课题、新成果,同时也分析、评估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筹划未来10年中国话语研究的发展战略。 20年前,“话语”“话语研究”还处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边缘;新时代里,它已不再寂寞,且有渗透整个学界的势头,我们相信这与国家和学界的自觉有关。然而问题是,人们对于其确切的定义、内涵及研究意义,往往并不清楚。而且,有些定义和概念过于片面,并不适合中国的情景与需求,也不利于话语研究的文化创新。因此,在我们描绘话语研究新发展的开头,先将“话语”的定义和概念,“话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加以说明。 出自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话语”(如英文里的"discourse",法语里的"discours")一词,至今在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科学讨论中,仍然处于一种概念纷繁或模糊的状态之中。有些用法指语句,有些指语篇或会话(如一封信、一席话),有些指语言使用中所表达的理念(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些指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如“中国梦”"新时代"),有些指特定文化群体的语言使用原则和规则(如“建立文论的中国话语”),有些指特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如媒体话语、课堂话语),有的与其他词混合,使其概念变得泛化或模糊不清(如舞蹈话语、建筑话语、话语权、话语体系)。 对话语做了较为系统研究、形成现代学派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要首推西方的“话语分析”(disco...
第1章 话语研究的国际图景…………………………………1
1.1 交际学的特性和特点……………………………1
1.2 话语分析的特性和特点……………………………3
1.3 交际学、话语分析的文化批评……………………7
第2章 话语研究的中国板块…………………………………11
2.1 国内外国语言学界的话语分析………11
2.1.1总体演进情况…………………………………2
2.1.2 研究热点和重点问题…………………………16
2.1.3 主要趋势和核心议题…………………………20
2.2 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话语研究…………………24
2.2.1 总体发展情况…………………………………24
2.2.2研究热点………………………………………29
2.2.3研究趋势及核心议题……………………31
2.3 小结 ………33
第3章 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37
3.1 交际学的文化局限……………………………………37
3.2 从交际学到文化话语研究 ………………………39
3.2.1 作为学术思湖的文化话语研究…………………39
3.2.2 作为学术范式的文化话语研究…………………41
3.2.3 作为学术平台的文化话语研究…………………45
3.3 小结……………………………………………46
第4章 文化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 …………………………49
4.1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体系……………………... 查看详情



 电子书
电子书
 在线购买
在线购买
 分享
分享











